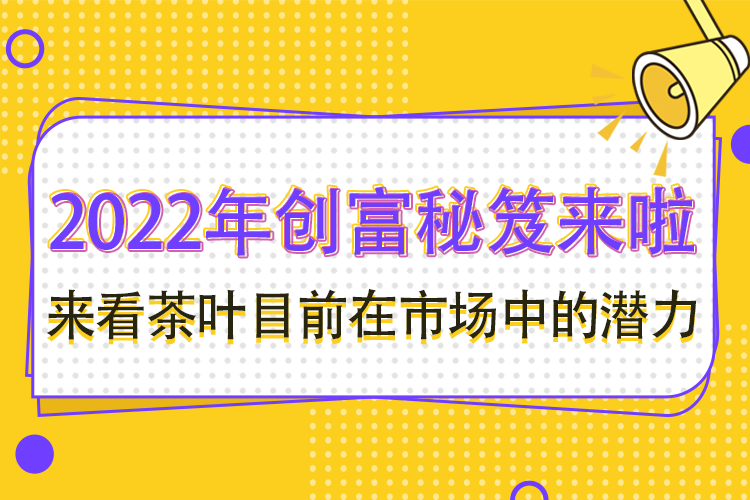相传与典籍记载哪个更可信?难说。但无疑问的是,典籍更权威,而传说更生动。比如传说很古之时,某个商队去往西域,正行进在苍茫大漠之中,忽逢大雨,无处躲避,马匹所驮茶叶皆被淋湿。商人们舍不得丢弃,雨过之后,在阳光下晒晒,又打包前行。商队来到驿站,见有牧人肚子疼痛,在地上打滚,询问之下,竟是消化不良导致肚子鼓胀,每年都有人罹患此症而不蹂躏。此时商队所携药物已用完,有人想到茶叶可以助消化,于是烧水煮茶。可打开茶包一看,茶叶已经发黑,并且生出了金黄色的“霉菌”。原来茶叶经雨后没全晒干主打包,便开始第二次发酵,颜色也变了,只是闻起来,倒有了特别的香气。救人要紧,也顾不得那么多,就将煮好的酱色茶水灌喂病人。奇迹发生了,病人鼓胀的肚子消瘪下去,疼痛亦随之消解。于是,黑色茶叶的神奇传遍了草原边地,自此之后,茶叶与盐巴一样,同为牧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了。
相传,带领这支商队的官员是西汉的班超;又相传,不是班超而是某个朝代的一位商人。这都没什么要紧,反正黑茶的传说传回了它的产地湖南安化,茶人们便丰富了以往的制作工艺,特意让它长出了那种金黄色的“霉菌”,那就是安化黑茶中独有的神奇的益生菌“金花”。黑茶就这样横空出世了,它有自己独特的香气、口感与功效。道法自然的黑茶,就这样从传说出发,穿越千年风雨,走到了当今的世人面前。
其实从现在的实物来看,安化的黑茶就是以前的黑毛茶,茶农初制一遍之后的茶,叫黑毛茶。虽说是初制,却也有采、炒、揉、渥、烘等五道工序,一道也马虎不得的。说来也算有幸,这每一道工序,都没有什么奇巧,我样样都做过。
采茶其实是书面语言,安化人不说采茶,说摘茶,且这个摘字,是念作“扎”字的去声的。摘茶有专门的工具,叫摘子,用铁片做成,像手指甲,是半月形的锋利刃口,有一指长的把,把背上还有个小指套,往右手中指上一套,摘子就像是新长出的一个器官了。摘子其实不仅用于摘茶,也可以和来打猪草。采茶时,你先选定一行茶树,然后左手扯过枝条,右手看准青枝绿叶一把握住,拇指与中指稍稍一用劲,听得轻微的一声咔嚓,连叶带茎就摘下来了。做黑毛茶不像采毛尖,只要是当年长出的就行,一年采两次,头茶采摘在立夏之后,那时茶树已有几寸长的新枝叶了。当新摘的茶叶握满手心了,便往斜挎的肓背上的布袋里一放。布袋俗名“叉口”,圆圆的大得能装下一个人。采茶季节,往山上打一望,你可看到星星点点布满山坡的白“叉口”。那个时候是人民公社,人们说说笑笑,消消停停,工效并不高,一天顶多摘上二三十斤鲜叶。嬉笑声中,当你听到某人突然发出夸张的尖叫,那一定是被茶树上的一种叫“霍辣子”的毛虫螫着了,那人的手背上会显出一道红色的印痕,并且火辣的又疼又痒。
茶叶采回之后,是不能用水洗的,直接就放到一口大铁锅里去炒,这道工序也叫杀青。铁锅是要烧得发红的,你站在锅前,双手抓紧一大团鲜茶叶放锅里,马上听见茶叶烫得扎扎响。这时你一手抓起三根枝的桐木权贴锅插下,另一手亦抓紧一把叶子顺便插往锅底,两手协调动作,不停推抵、翻起、抖开,使茶叶得到充分的炒掉,发软发蔫而不至于炒焦烧糊。炒茶是个技术活,我所在的生产队只有三四个人会,我也学会了,炒过十几锅,但那是出于逞能或者显摆,有点玩票的味道。
揉茶在某些专业书上叫喘茶,而在我老家,都叫揉茶。这个揉茶以前是足旁,当然就是用脚蹂了。一锅鲜茶叶炒好之后,就会被放到堂屋有晒簟的地面上。蹂茶人将两支胳膊搁在架好的木杠上,以支撑住身体,先用脚将那锅热茶叶扫拢,团成一团,然后两脚交替喘紧、搓揉、滚动它,从晒簟这一头滚到那一头,又从那一头滚到这一头,往复不休,直到茶叶团彻底柔软,茶汁充分地泌出。以脚蹂茶实在太劳累,所以到大集体时期,茶叶的揉捻都改用机器了。
渥堆就是将揉好的茶团抖散,堆在一隅,让其自行发酵。但渥堆多久,渥到什么程度,那是有经验的制茶人才晓得的,不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。我曾经好奇地将手放在茶堆上试探,仿佛摸到了它的呼吸,它的体温,甚至还有脉搏。它的内部正在发生某种奇妙的我所不知的变化。安化黑茶好多说不清的奥妙之处,就在于它的这一渥。一般过夜之后,茶叶已成油黑色。此时再加蹂一次,约十五分钟,名曰复脚(现在叫复揉),之后再次抖散以整理其形状,这个时候,因蹂出的茶汁充分浸染,茶叶呈现出油黑发亮的色态。
渥堆整理过后的茶叶,就要拿去烘干了。烘茶是有专门的设施的,我们叫它茶焙房,其实就是搭一个简易却又能长期使用的棚子,棚内砌一有七孔的七星灶,灶上方是长丈余、宽八尺的焙炕,宛如一架巨大的床,上铺粗篾编织的竹簾。将茶叶均匀撒铺在簾子上,然后将火生起来慢慢烘烤。当然,如果当时有太阳,是可以先晒上一天半天再烘的,这样可以节省柴火减少成本。所用柴火必须是松明,松明火烘熏出来的茶叶才有黑茶特有的香气,而松明,我们乡下人也叫松膏,是极为难得的,只有将老年枯死的松树劈开,才能得到几块。烘茶是件轻松的活也是件有技术含量的活,村里常常将它交给炎伯。炎伯是个老单身,喜出汗,他在茶焙房烧火时,即使坐着不动,也见他胸前背后湿漉漉的。而他烧出的蓝色烟雾,总是远远的就看得见,跟着风飘过来飘过去的。我想起了匡国泰写炊烟的诗:姐姐的辫子,早晨梳一次,晚上又梳一次。采茶季节,烘房上空那缕蓝色烟雾是从早到晚飘个不停的,那又是谁的辫子呢?
茶叶烘干了,黑毛茶就制成了,余下的事就是将它送往供销社了。在人民公社时代,乡下所有的土特产,都由供销社统一收购。送茶是件麻烦的事,因为茶叶松散,装茶叶的篾篓体积庞大,而山路很长很弯很狭窄,挑茶出山不光需要力气,还需要技巧。所以,队里一般不派年少的我送茶。我唯一的一次送茶,是因为负责送一个尾数,才得以成行。我用两只叉口袋子,挑着大约五十来斤黑毛茶,晃晃悠悠地到了五里之外的河曲溪供销社,过完秤后,就和队里所有送茶人一起,伏在柜台上,每人一两烧酒二两饼干,嘴巴咂得啧啧响,那种满足,那份惬意,是如今最高档次的酒店也带给不了你的。还记得,每百斤黑毛茶的售价是55元,队里每年要交售给国家十几担。老家每个工时的价值有七角五分钱,比别的地方高,黑毛茶的收入是占了较大比重的。老家的茶园不多,但都有数百年的历史,可以说,我们是在吃祖宗饭,喝祖宗茶。
打开微信,点击底部的“发现”,
使用“扫一扫”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。